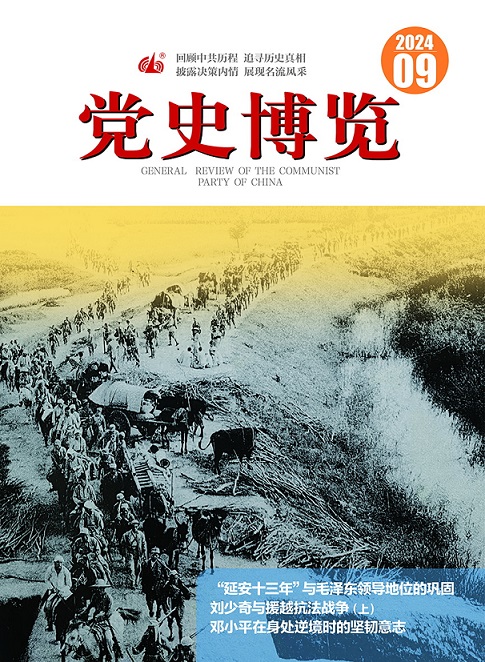當(dāng)前位置: 網(wǎng)站首頁(yè) > 歲月如歌
年輕時(shí)候的金學(xué)曙醫(yī)生
冒險(xiǎn)義助志士的“白衣天使”
1949年5月初,上海解放前夕,在霞飛路虹橋療養(yǎng)院一處僻靜的角落里,夜深人靜,只有一點(diǎn)微弱的火光,映出一張年輕又嚴(yán)肅的臉。看真了,那是個(gè)一襲白衣的女青年,披著深色外套,盡量壓低身體,遮擋著一堆正在燃燒的紙張。夜色中,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顫抖,不時(shí)警惕地環(huán)視周圍,生怕被人察覺(jué)。
與此同時(shí),不遠(yuǎn)處的虹橋療養(yǎng)院206號(hào)病房,民盟主席張瀾正愁眉不展,枯坐沉思,旁邊是同樣憂心忡忡的羅隆基,他背著手在病房里踱步,十分緊張。就在相鄰的205病房,三名制服大漢正在打牌聊天,配槍在燈下泛著烏黝黝的藍(lán)光。
原來(lái),1949年4月20日,國(guó)民黨政府拒絕了中國(guó)共產(chǎn)黨提出的和平條件。21日,解放軍百萬(wàn)雄師打響了渡江戰(zhàn)役,23日就解放了南京。26日,蔣介石趕到上海,當(dāng)天就緊急召見一批軍政要員,除了給部下打氣,還要屠殺一批革命志士泄恨。他給毛人鳳發(fā)去密電:“……所有在押的共產(chǎn)黨、民主分子、嫌疑犯,包括保釋出來(lái)的政治犯,一律處置,不給共產(chǎn)黨留下活口……”其中就包括民盟負(fù)責(zé)人張瀾和羅隆基。
早在1947年10月就已被國(guó)民黨宣布為“非法團(tuán)體”,勒令解散的民盟,總部已由沈鈞儒等赴港組織恢復(fù),而主席張瀾則繼續(xù)留滬為總部籌款,并策動(dòng)西南軍政首腦起義。這大大觸怒了蔣介石。既有蔣介石的密電,1949年5月9日,國(guó)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便準(zhǔn)備拘捕張、羅,但因張、羅是很有影響力的民主人士,他們?cè)緮M定的直接刺殺計(jì)劃被迫擱淺,加之有事先被中共地下黨爭(zhēng)取過(guò)來(lái)的閻錦文從中斡旋,拘捕改為就院監(jiān)守,張、羅被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(yǎng)院206號(hào)病房,由三名警備隊(duì)員住在205病房,晝夜輪班看守。
當(dāng)時(shí),除了貼身看守的警員,張、羅所住病區(qū)也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十多名特務(wù)包圍。隨著解放軍不斷逼近上海,周恩來(lái)領(lǐng)導(dǎo)的中共地下黨預(yù)見到,如不及時(shí)營(yíng)救,張、羅在國(guó)民黨當(dāng)局撤離上海之前必遭毒手,情勢(shì)非常緊急。
張瀾和羅隆基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命在旦夕,但比自身性命更堪憂慮的,是民盟大批愛(ài)國(guó)志士的生命安全。他們手握重要文件,一旦被抄,必將令愛(ài)國(guó)者們?cè)跀橙俗詈蟮寞偪穹磽渲斜话磮D索驥,大量屠殺,給革命事業(yè)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,后果不堪設(shè)想。
張瀾急于銷毀手里的大批文件資料,但苦于自己入院不久,情況不甚熟悉,不知何人可信,雖有丁院長(zhǎng)、鄭院長(zhǎng)等相助,但他們目標(biāo)太大,容易引起特務(wù)軍警的注意,便讓1947年即已入院治療的羅隆基去設(shè)法。羅隆基想盡辦法,終于避開特務(wù)們的嚴(yán)密監(jiān)視,悄悄地找到他最信任的名叫金學(xué)曙的小醫(yī)生,托以重任。
在此之前,羅隆基住院期間,金學(xué)曙就曾多次幫助過(guò)他傳遞信息,開展工作,因此羅隆基才對(duì)她格外信任,找她幫助張瀾銷毀文件。但今次不同往日,金學(xué)曙知道,虹橋療養(yǎng)院里里外外都是如狼似虎的國(guó)民黨軍警特務(wù),她還知道隨著解放軍逼近上海,大戰(zhàn)在即,國(guó)民黨正在大肆搜捕、殺害進(jìn)步人士和地下黨員。雖然在各方斡旋下,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馬上對(duì)張、羅下手,但自己只是一名醫(yī)務(wù)人員,無(wú)人保護(hù),幫助張、羅的行為一旦被發(fā)現(xiàn),特務(wù)軍警們肯定會(huì)毫不猶豫地殺害自己,除了打擊報(bào)復(fù),還可“殺一儆百”,起到恐嚇威懾作用。
金學(xué)曙沒(méi)有上過(guò)戰(zhàn)場(chǎng),手里只拿過(guò)醫(yī)療器械,但日寇的炸彈令她父母雙亡,成為孤兒的童年經(jīng)歷,給了她非同一般的堅(jiān)毅和對(duì)戰(zhàn)爭(zhēng)與和平的深刻認(rèn)識(shí)。她深知,唯有順應(yīng)民心的隊(duì)伍,才能為人民爭(zhēng)取到真正的和平,而自己冒著生命危險(xiǎn)支持的,不正是這樣的隊(duì)伍嗎?
為了國(guó)家和民族的未來(lái),個(gè)人的生死存亡又何足惜。雖有性命之憂,但是大義當(dāng)前,年輕的金學(xué)曙,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,點(diǎn)頭答應(yīng)了羅隆基的請(qǐng)求。經(jīng)過(guò)一番密斟,她告訴羅隆基自己晚間會(huì)來(lái)打針?biāo)退帲璐藱C(jī)會(huì)可先轉(zhuǎn)移一小部分文件,讓他和張瀾提前做好準(zhǔn)備。
就這樣,金學(xué)曙一次一次成功應(yīng)付了特務(wù)們兇神惡煞的威脅,不懷好意的盤問(wèn),還有擦肩而過(guò)的各種危險(xiǎn)。她利用自身行醫(yī)問(wèn)診的便利,憑借過(guò)人的膽識(shí)和機(jī)智,成功避開特務(wù)軍警的耳目,歷經(jīng)多次驚心動(dòng)魄,一波三折的迂回過(guò)程,終于把張瀾和羅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秘密轉(zhuǎn)移,并分批銷毀。
虹橋療養(yǎng)院畢竟人多眼雜,1935年鄒韜奮邀戈公振來(lái)滬,僅七天戈公振就在虹橋療養(yǎng)院神秘死亡,論及其病因和虹橋療養(yǎng)院首屈一指的醫(yī)療條件,的確匪夷所思。考慮到安全因素,金學(xué)曙清醒地意識(shí)到,在嚴(yán)峻考驗(yàn)面前,任何大意疏忽都會(huì)給革命事業(yè)帶來(lái)慘痛損失,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托付。因此,無(wú)論是平時(shí)相好的姐妹,還是一直敬重的院領(lǐng)導(dǎo),她都不敢透露一點(diǎn)消息,也不敢尋求任何幫助,生怕危急關(guān)頭,有人變節(jié),導(dǎo)致功虧一簣。
因此,這一切,金學(xué)曙都要一個(gè)人,在夜深人靜的時(shí)候獨(dú)自悄悄完成。于是,便有了開頭那看似平靜,實(shí)則萬(wàn)分兇險(xiǎn)的一幕。

1949年,丁惠康(右)、張瀾(中)、羅隆基在上海虹橋療養(yǎng)院
從羅隆基1947年入住虹橋療養(yǎng)院治療肺結(jié)核和糖尿病,到張瀾、羅隆基1949年5月24日晚最終被救脫險(xiǎn),這期間發(fā)生的那些驚心動(dòng)魄的故事,傳誦甚廣,很久以后,還被搬上了電影《建國(guó)大業(yè)》的大銀幕。但是,金學(xué)曙醫(yī)生的義舉卻始終鮮為人知。
建國(guó)后,張、羅離滬赴京,出席了中國(guó)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(huì)議籌備會(huì)。在中國(guó)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(huì)議上,張瀾當(dāng)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,羅隆基于新中國(guó)成立后被任命為政務(wù)委員。金學(xué)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來(lái)到北京,但她從未主動(dòng)聯(lián)系過(guò)張瀾和羅隆基。
解放后,營(yíng)救張瀾、羅隆基有功的閻錦文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任專員。他每次到北京,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張瀾都必設(shè)家宴招待,親自作陪。后閻錦文長(zhǎng)駐北京,并受邀擔(dān)任了宣武區(qū)政協(xié)委員。
“文革”期間,閻錦文受到迫害。“文革”后,在落實(shí)政策中,閻錦文沒(méi)有其他要求,只向全國(guó)政協(xié)提出一個(gè)要求,就是將其由退休改為離休。表面上看,這涉及閻錦文是否能享受離休待遇的問(wèn)題,實(shí)際上,究竟是退休還是離休,則是界定他參加革命工作時(shí)間的大事。對(duì)此,全國(guó)政協(xié)主席鄧穎超親自做出批示:“……營(yíng)救張瀾、羅隆基在當(dāng)時(shí)是件大事。所以,我印象較深。閻錦文先生對(duì)中國(guó)革命是有貢獻(xiàn)的,凡是對(duì)我們黨、國(guó)家和人民做過(guò)好事的人,我們是不應(yīng)忘記的,更不能虧待人家……”。此后,按黨的干部政策,閻錦文參加革命工作時(shí)間從他營(yíng)救張瀾、羅隆基之日起算,由此他獲得離休干部身份。
后來(lái),了解內(nèi)情的虹橋療養(yǎng)院老友來(lái)京看望金醫(yī)生的時(shí)候,告訴了她閻錦文的事情,勸她也給自己想想辦法,爭(zhēng)取一下離休待遇。金醫(yī)生聽后,笑著說(shuō),人家做了那么大的事情,我只做了一點(diǎn)點(diǎn)小事,怎么能向國(guó)家要待遇?我就是個(gè)大夫,幫助病人,都是應(yīng)該做的。老友誠(chéng)摯地說(shuō),離休干部在醫(yī)療報(bào)銷等各方面都有更高待遇,而且這不單是為了經(jīng)濟(jì)考慮,還是一個(gè)黨員一輩子的大事,一定要搞清楚的呀。金醫(yī)生還是那句話:“我做的都是應(yīng)該做的事,就不去給國(guó)家添麻煩了。”
多年后,當(dāng)金醫(yī)生病重急需特殊藥品時(shí),卻不能報(bào)銷,也因?yàn)獒t(yī)院床位緊張而無(wú)法及時(shí)住院治療。直到金醫(yī)生2014年去世,她始終未將自己解放前的這段經(jīng)歷向組織反映,也從未向組織上提出過(guò)任何要求。
告別十里洋場(chǎng)的革命伴侶
1948年,在一場(chǎng)樸素的婚禮上,金學(xué)曙醫(yī)生與鐵路工程專家施錫祉在上海結(jié)為伉儷。禮成后,一位鶴發(fā)長(zhǎng)髯,滿面微笑的老人上前向這對(duì)新人表示恭喜。這位老人便是他們的證婚人,也是日后對(duì)他們的一生產(chǎn)生了重要影響的愛(ài)國(guó)民主人士陳叔通。陳叔通是浙江杭州人,曾執(zhí)教于杭州求是書院。求是書院是浙江大學(xué)前身,在當(dāng)時(shí)培養(yǎng)出了一大批愛(ài)國(guó)精英,其中就有金醫(yī)生的公公、民國(guó)開國(guó)名將施承志,以及錢學(xué)森的父親錢均夫。施承志和錢均夫是世交,關(guān)系親厚,他們又都與亦師亦友的陳叔通感情甚篤。
因此,盡管當(dāng)時(shí)陳叔通處境十分危險(xiǎn),他還是把個(gè)人安危置之度外,為金學(xué)曙和施錫祉證婚。原來(lái),1947年,陳叔通發(fā)動(dòng)“十老上書”營(yíng)救被捕進(jìn)步學(xué)生事件之后,國(guó)民黨政府加緊了對(duì)國(guó)統(tǒng)區(qū)共產(chǎn)黨人和革命人民的鎮(zhèn)壓,時(shí)在上海的部份民主人士被迫轉(zhuǎn)入地下或撤離。陳叔通則留在上海,堅(jiān)持斗爭(zhēng),并與中共保持著密切聯(lián)系。白色恐怖之下,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曾托人轉(zhuǎn)告陳叔通說(shuō):“我已兩次把你的大名從共黨嫌疑分子名單上勾了去,今后你若再要活動(dòng),我就無(wú)能為力了!”陳叔通卻一笑置之,請(qǐng)人轉(zhuǎn)告陳布雷:“我也勸你早日洗手,棄暗投明。”
金學(xué)曙和丈夫施錫祉正是受了世交長(zhǎng)輩陳叔通的影響,自新婚伊始,就不單沉浸在二人的小家庭里,兩顆年輕的心,時(shí)刻關(guān)切著國(guó)家和民族的命運(yùn),在解放前的上海,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,一步步向著光明靠攏。新婚燕爾的金醫(yī)生,能夠不顧個(gè)人安危,義助張瀾、羅隆基,這與叔老的言傳身教不無(wú)關(guān)系。
1949年5月,上海解放后,陳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從北平回到上海,宣傳黨的方針政策,發(fā)起成立工商界勞軍分會(huì),慰勞解放軍,廣泛動(dòng)員和聯(lián)絡(luò)社會(huì)各界積極參與。在這火熱的氛圍里,金學(xué)曙和丈夫慷慨解囊,把二人小家庭的全部積蓄都捐獻(xiàn)了出來(lái),金醫(yī)生還積極參加?jì)D女屆的勞軍活動(dòng),為解放軍貢獻(xiàn)自己的一份力量。7月,勞軍總會(huì)在陳叔通的主持下,以捐獻(xiàn)、義賣等各種形式,取得了認(rèn)繳款物87億元(舊幣)的卓著成績(jī),陳毅市長(zhǎng)特此親筆書寫了“勞軍模范”四個(gè)字,感謝各界人士的厚愛(ài)和熱情。
新中國(guó)剛一成立,金學(xué)曙和丈夫即雙雙離開上海,奔赴百業(yè)待興的北京,這也與叔老的影響有莫大的關(guān)系。
早在1949年4月,渡江戰(zhàn)役勝利之時(shí),黨中央、毛主席就已高瞻遠(yuǎn)矚地及時(shí)地把解放、接管、管理上海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(lái)。1949年4月7日,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鄧小平、饒漱石、陳毅電,指出:“……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(méi)有自由資產(chǎn)階級(jí)的幫助,可能發(fā)生很大的困難,很難對(duì)付帝國(guó)主義、官僚資本及國(guó)民黨的強(qiáng)大的聯(lián)合勢(shì)力,很難使這些敵對(duì)勢(shì)力處于孤立。這件事,你們現(xiàn)在就應(yīng)開始注意。因此,請(qǐng)你們考慮,是否有必要在沒(méi)有占領(lǐng)上海以前,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。而在占領(lǐng)上海以后,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。”這一電報(bào)表明,上海解放前夕,毛澤東就提出了應(yīng)當(dāng)注意吸收更多黨外人士參加工作,以克服面臨的困難。
當(dāng)時(shí)的上海聚集了一批全國(guó)各領(lǐng)域的頂尖人才。金醫(yī)生的丈夫施錫祉即是當(dāng)時(shí)全國(guó)屈指可數(shù)的通曉德、英、俄三種外語(yǔ)的土木工程專家,而身為西醫(yī)的金學(xué)曙在缺醫(yī)少藥的建國(guó)初期也是極為稀缺的醫(yī)務(wù)人才。且夫妻二人都是自學(xué)生時(shí)代便在上海學(xué)習(xí)生活,10余年來(lái)已習(xí)慣了上海的水土,當(dāng)時(shí)上海的生活條件也更加優(yōu)越,繼續(xù)在上海工作,對(duì)兩人來(lái)講確實(shí)是比較好的選擇。
1949年6月,陳叔通從上海來(lái)到北京,被推為新政治協(xié)商會(huì)議籌備會(huì)副主任,并出席了開國(guó)大典。新中國(guó)成立后,他擔(dān)任了全國(guó)人大常委會(huì)副委員長(zhǎng)、全國(guó)政協(xié)副主席、全國(guó)工商聯(lián)主任委員等職。在北京定居后,陳叔通曾告知金醫(yī)生夫婦他在北京頭發(fā)胡同56號(hào)居住,隨時(shí)歡迎來(lái)訪。但考慮到叔老事務(wù)繁忙,金醫(yī)生夫婦一直都沒(méi)有去麻煩過(guò)陳叔通。
看著一大把年紀(jì)的陳叔通老人不辭辛苦,為了新中國(guó)來(lái)回奔波,更離滬赴京共襄大業(yè),兩個(gè)年輕人感動(dòng)之余,決心以叔老為榜樣,到新中國(guó)更需要他們的地方去,到人民更需要他們的地方去。國(guó)家要建設(shè)新中國(guó)的鐵路,北京鐵道部急需工程技術(shù)專家。人民日?qǐng)?bào)社由河北省平山縣里莊遷至北京,報(bào)社急需專業(yè)醫(yī)生。一切為了新中國(guó)。拋掉了上海辛苦營(yíng)造的小家,帶著簡(jiǎn)單的行李,金醫(yī)生抱著剛出生的女兒,和丈夫肩并肩,離開了上海十里洋場(chǎng),奔赴熱火朝天的北京。一對(duì)革命伴侶,自此開始譜寫一生與新中國(guó)同呼吸、共命運(yùn)的新篇章。